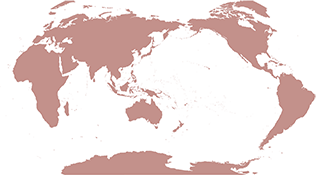
如果生命快要走向終點,如何擁有一個平靜、從容、被理解與被善待的“最后一程”?“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擴大“安寧療護服務供給”。在快速老齡化的當下,家庭照護能力不斷減弱,機構資源日益緊張,社區安寧療護成為一道溫和而堅實的橋梁。
死亡,需要從容準備與系統應對
傳統醫療體系往往將就醫視為一種“例外狀態”。身體的失序導致日常生活節奏被打亂,人們在診室與藥物面前不再談論尊嚴、舒適和安慰。人們默認在這里履行“交換”的契約——為了治病和重建健康,“受苦”的代價是必要的。遺憾的是,對于臨終患者而言,治療與生活已難以分割,無論受多少苦,他們都無法再回到“常態”。此時,患者托身的醫療救治,就成為與死亡之間的一場無法取勝的“戰斗”。
安寧療護的出現,正是對這種醫學邏輯的反思與修正。它與死亡和解,通過陪伴、關懷與理解,構建一種涵蓋身體、心理、靈性的綜合關懷,讓生命的最后旅程變得平和而完整。從2017年國家啟動安寧療護試點工作以來,這項服務如今已經開始走進城市社區。在北京,一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轉型建立了安寧療護中心,由醫生、護士、社工和志愿者組成的靈活團隊穿梭在病床與家庭之間。他們不僅控制疼痛,還耐心傾聽患者的故事,幫助他們整理心愿,陪伴家屬度過心理上的煎熬。
從大型醫院到社區機構,安寧療護的延伸來源于供方與需方的“雙向奔赴”。一方面,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因其床位靈活、服務連貫,更適合提供以個體為中心的連續照護。同時,作為公共衛生體系的基層環節,社區更能承擔起將安寧療護作為一種公共福利的責任。另一方面,居家和鄰里空間讓“告別”不再遙遠。對許多人而言,能在熟悉的社區里、親人的陪伴中安然離世,是對生命最后尊重的表達。
這場轉型不僅是單純的醫療創新,更是一次社會文明的躍遷。它促使社會重新認識到:死亡不僅是醫院里的醫療行為,還是一個社會事件和公共議題,需要全社會共同承擔責任。
社區實踐中的多重困境
盡管安寧療護理念日益受到重視,但它在城市社區的推進之路依然布滿荊棘。
社會認知的滯后與偏差成為第一道屏障。雖然多數居民對“安寧療護”一詞不再陌生,但調查顯示真正愿意接受的不足三分之二。有人擔心這意味著“放棄治療”,有人害怕觸及死亡話題。醫生和護士也常陷入兩難:一邊是患者家屬在情感與倫理里的掙扎,另一邊是制度對他們缺乏明確的激勵與保障。
安寧療護講求長期、連續、全方位的整合照護,但社區醫療機構的主要職能更多停留在“看病開藥”的環節,績效考核看重的是“治愈率”“出院數”。這種錯位使社區機構常在患者需求與行政定位之間艱難平衡。北京市一家社區安寧療護中心的負責人坦言:“我們今年才爭取到一名專職社工,其他工作基本上靠醫護人員額外承擔。”

醫護人員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安寧療護病房內查房并詢問患者身體情況 徐昱 攝
規范的缺失,則從制度上制約了社區安寧療護的標準化發展。我國現有的安寧療護政策多圍繞醫院場景設計,對社區及居家環境中的服務流程、文書規范、質量評價等缺乏細致指引。安寧療護投入高、收益低,醫保報銷體系對舒適護理、心理支持等項目覆蓋不足,使得許多社區機構長期依賴“情懷投入”維持運行。
此外,信息共享與轉診機制的不暢,使社區與醫院、家庭之間的服務銜接步履維艱。尤其麻醉類鎮痛藥物在居家場景的使用限制,更從制度層面阻礙了專業服務向家庭的有效延伸。個別社區依靠醫護人員自發探索,提供居家上門的安寧療護服務,卻因缺乏體系支持而中止。
不僅是醫院或社區的任務
盡管挑戰重重,但社區安寧療護的發展前景仍然可期,關鍵在于促進理念、政策與實務的多維協同,讓服務既專業又可持續。
首先,認知調適應該被視為前提。安寧療護的推進需要一場全社會共同參與的“善終教育”,教會人們如何溫柔地告別。可以通過社區講座、健康宣教、媒體傳播,讓更多家庭理解“善終”并非冷漠,而是尊重生命的另一種方式。
其次,資源必須跟上。醫療力量要真正“下沉”到社區,讓社區衛生機構不僅能看病,還能提供照護,讓有限的床位、設備與財政補貼更精準地流向需要的人群。一支穩定的團隊同樣重要——醫生、護士、社工、志愿者各司其職,通過系統培訓、職業支持和職業發展路徑的建設與完善,守住職業尊嚴。
最后,制度支撐很關鍵。安寧療護需要有標準可循、有保障可依。醫保政策、服務質量評估、合理的費用補貼,都是讓機構愿意做、能持續做的關鍵。而借助信息化手段,打通社區、醫院與家庭之間的數據壁壘,也能讓照護更順暢——病情評估、用藥管理、居家疼痛緩解,都能在一個系統里被看見、被記錄、被接力。
安寧療護不應僅是醫院或社區的任務,而應上升為一項具有普惠意義的社會公共事業。它需要突破城市社區的物理邊界,超越傳統醫療場域的功能局限,成為構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務體系的重要一環。理想狀態下,安寧療護應融入社會治理的整體框架,通過政策引導、資源整合與社會參與,逐步形成覆蓋城鄉、銜接機構與居家社區的全流程關懷網絡,讓生命的謝幕同樣充滿尊嚴、關懷與體面。(作者陸杰華系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健康學院教授;作者戚政燁系北京大學應對老齡化國家戰略研究中心研究助理)